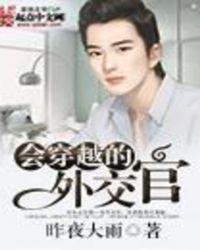京鸿小说网>青春 悸动 > 第32章 被回忆抓住和凌迟(第1页)
第32章 被回忆抓住和凌迟(第1页)
大汗淋漓的中午。
还在念小学的时候,礼拜二是我做值日的日子,对于值日这件事情其实我非常的抵触,倒不是因为我懒而不愿意去做,是因为我在这件事情上实在被折腾得够了。值日表是没有统一的安排的,轮到了这一组打扫卫生的日子,组长可以随意安排哪个组员干什么,所以基本上我都会在大夏天被要求去走廊上拖地,而冬天擦窗台的任务肯定是落在我身上的。我的手很小,所以不可能像有些男生样把抹布摊开,然后直接用手抹就行了,因为如果这样,抹布的受力面只有我手掌大小,其他的部分肯定会甩来甩去,脏水溅到我的手背上,又冰又臭。我必须把抹布对折再对折,然后握在手中,再慢慢地去擦,因为如果擦不干净,组长是不会让我歇着的。
还有一次更过分,那天正好轮到我擦黑板,上完班主任的语文课下一节是音乐课,我刚好没带这科的书,硬着头皮去隔壁班向幼稚园同班的同学借了一本,打算回到教室在擦黑板。刚想把书放到座位上,就听到班主任叫了我一声,我知道肯定没什么好事,下了课她竟然还没走,我看着她,她朝我白了一眼,用手里的红笔敲了敲身后的黑板。
——下课不知道擦黑板?懒死你算了,这个学期黑板全都你来擦。
然后她佯装生气地夹了教科书出去了,我连解释的机会都没有,然而我也并不想解释,周围有的人在笑我,没笑的都是没听到的,我捏了捏手里的音乐书,但我不能捏皱它,因为它不是我的。不止是音乐书,我身上的衣服,我座位上的书包,我笔袋里的水笔,我现在拥有的任何东西都不是我的,都是用邓心给顾昕昕的生活费买来的,在这个世界上,任何东西都还不属于我,所以我不能反抗,那个时候,直到现在,我都没有资本。
之后我就真的任命地擦了一个学期的黑板,粉笔灰落在脸上的感觉不好,有些老师字迹很重,有时候粉笔灰会嵌在黑板上的小凹痕里,通常擦完这种老师的板书,我整张脸会被粉笔灰弄得通红,但我学不会用手捂住自己的脸,我得让所有人看着,我没有哭啊。
我所有的丑样都可以给你们看,你们可以尽情笑我,或者不屑一顾,但我是不会哭的,所以总有一天你们会明白你们有多失败,多无聊。一方不心悦诚服,另一方怎么也不算做赢,反正我是这么想的,对吧?
那个中午是十月的时候来的,已经是夏末秋初,早午晚的温差很大,早上我裹着风衣出门,中午就已经热得要卷起袖子。我还没来得及把外套脱掉,就被组长赶出去拖地,我一出门口,太阳光马上激得我眼前一片亮斑在飘动,我有轻微的飞蚊症,看不得太亮的东西,这么一个艳阳天,不好好折磨我确实挺可惜的。
我握了握手里的拖把,这分量实在很不正常,我知道他肯定是把拖把拿去水槽浸了一浸,故意不把水绞干就拿来让我拖地。我假装不知道,反正也不是第一次了。
那个学期我的组长叫林晨,长得比我还矮,浑身是肉,但一点也没有敦实的感觉,膘肉横生也没能埋没他尖酸刻薄的天赋。
他是上个学期新转进来的学生,科学和数学的成绩特别好,班主任就特别爱看这种学生,据说以前她教过的几个学生上了复旦当了年轻教授,吃过这种甜头,自然而然想要培养下一批,知道没什么希望的,就搁到一边不做重点培养,我想我连后者都算不上,因为她培养出的我除了糯性以外什么都没有。
她还经常以炫耀她学生那些事迹为班会课的主要内容。我觉得这种说法未免可笑,凭什么人家不感谢高中和初中老师,直接横跨六年来感谢连毛都没长齐的岁月里可能只是夸过他字写得工整的小学老师。照这么说,他是不是更应该感谢妇科医院里的接生护士,要不是她当时在他屁股上那浑然天成响当当的一掌,也许今天他也不会活得这么清新脱俗。
我不知道那些学生是怎么想的,反正要是有一天我成功了,我有了话语权,我想我要在镜头前微笑着说,我的小学班主任是某某,但是我觉得她是个bitch。
我不停地幻想台下观众舌桥不下的表情,脸上又是一阵灼热,拖把还是太重,我用了一下力,被走廊上不平的地制住了力,手一松,拖把就掉在了地上。我低下头的去捡,看到一双鞋带已经脏成了灰色的球鞋,我有点这方面的强迫症,最看不惯一双鞋子鞋面还是干净的,鞋带却脏成这样,但这并不是洁癖,因为如果鞋面也是脏的,我无话可说。
球鞋的主人是林晨,我看他的时候他正装老成地扶镜框一副来视察的样子,我想不明白这么点大的小孩子脸上怎么老是会有这种老气横秋的表情。
——你扫完了?
我用手背擦了擦额头上的汗点了点头,有几根头发已经被汗液黏在了一起,这样会显得我的头发特别少。我知道第一次肯定是不会通过的,我握紧拖把跟在他后面把他踩脏的地又重新拖了一边,他朝我招招手让我过去,我走到他面前他一把抢走我的拖把,一脚踩住扫把头上纱绳状的布条,用脚蹭了好几下。
——看到没有,这才叫干净,你这样也叫拖过了?
我听话地去看他脚下的那块地,立刻哭笑不得,这地和刚才有什么区别,但是既然他说这样很干净,那我就姑且这么认为吧,因为没人给我权利反抗。他把拖把甩给我,拖把的杆一下子砸在我骨节上,我用另一只手胡乱抓过又要倒地的拖把。林晨眼睛里只闪过几秒的动摇,然后进了教室,在他进教室之前还不忘继续数落我一句。
——说你懒你还真懒。
我耸了耸肩想要表示我无所谓,动作却略显僵硬,我感觉到喉咙里一阵反酸,我知道我想哭了,我强迫自己去想别的事,因为有时候越是在心里叫自己不要哭就越是容易哭出来,心里暗示的关键词是在乎。
我又从教室后门口一直拖到了前门口,刚想进去叫林晨出来再检查,看到他正倚在门上跟数学课代表聊天,声音不响但我恰好能听见,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故意要让我听见的,我自认为小学生应该没有这种城府。
——她怎么还在拖地啊?
——我就不放过她,她能拿我怎么样,让她爸来打我?她哪有爸爸啊。
我还没来得及去酝酿和控制,眼泪就掉在了我的袖口,一瞬间我几乎怀疑这只是从楼上漏下来的水,想到防备已经晚了,泪腺的闸被沉淀在空气里的对话氧化了,我想用力地去拧紧开关,却让泪水越加汹涌。我不相信他们没有看到,我彻底输了,他们又说说笑笑地进去了,我的刘海不长,根本遮不住多少地方,只能弯着腰直视着地面才能保证自己的脸不被别人看到。
但是这无济于事,我知道他们看得到,来来往往的隔壁班的同学看得到,捧着大叠讲义匆匆而过的教导主任看得到。坐在隔壁班后门口就离我五米远正在晒太阳的数学老师看得到。但他们没有停下来,也什么都没有说,所以我也就什么都没说。哭到后面难免会有止不住的抽泣声,我不停吸着鼻子,感觉喉咙里吞下了好多液体,他们一定在心里议论我笑我,但我哭了,是我输了。
我不知道那天中午我是怎么收好拖把回了教室,那天在走廊里拖了多久的地,日月还是年,我感觉所有用来形容时间的量词都没法去度量那种漫长的难受,我的肩膀,连着我的整颗心都在发抖,在炽热的大中午,被人心冻得瑟瑟发抖。
回忆到了这里,我已经完全脱离了原本想要为了思考问题而去曾经里取证的轨道。其实我只不过想说,那件事情让我知道了,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点,笑点泪点心动点,曾经自认为是疾风里的劲草的我,不还是被几句凉薄的传言给打倒了。
所以我未必只能从他的兴趣下手,只要能成功地拖住他问个清楚,我就算是死缠烂打或者劈头盖脸骂他一顿也要去做,我只知道,过了今晚这个时间的临界线,一切的事情我都没有勇气去做了。
我想了想有什么事情能把张孟轩弄哭,但脑子里全是他笑得比强奸了小龙女的尹志平还贱的样子,要把他弄哭是没什么可能的了,我们认识也有一个多月了,我对他的了解却一直都没加深过。我对陈逸的关注要多得多,张孟轩是站在我这一边的,但是说到底,他是站在陈逸那一边的,他对陈逸所有的事情都很在乎,我想现在能挑动他心里弦的那个关键词应该就是困扰着陈逸的,古湘的病,至少我知道的只有这件事了。
这样事情就棘手了,因为我要说的就是这件事,我想套出他的话,我由果溯因,结果又把这个因绕了回去。
时间一分一秒过,从张孟轩上线已经过了六分钟了,虽然他并不是每次都凑好了十分钟之后就开游戏,但是我的时间真的不多了。我有了一个自暴自弃的想法,其实此刻我已经不能有别的任何想法了,我从前有太多的机会可以搏一搏,都因为瞻前顾后而放弃了,但是现在我已经没有耐心了。
我打开张孟轩的聊天窗口,没看屏幕就用手在键盘上按了一几下然后按下回车发送了出去,我不确定有没有打错字,但我这时候要是再去看屏幕,我肯定会犹豫。
——古湘的病能治好吗?
我发出去的瞬间就看到他的状态从在线变成了离开,是我晚了一步,刚好没赶上那个时间,还是他其实看到了然后不知所措地改了状态,或者根本是我猜错了,这两件事情其实压根没有联系,得病的另有其人。我呈大字型仰躺在床上,我很少以这么嚣张的姿势躺着,我的手心覆上我的眼睛,眼皮上就全是细细密密的冷汗。
我们每个人都会在某些时候,在心底升起另自己都作呕的念头,都会想象自己是电影里的大坏蛋,反派奸角,要把别人对自己的凌迟加之于不相干的人身上。有的人敢去做,有的人不敢,于是世界上才有了坏人好人之分。
那些年里我还不懂这些,所以我一直以为自己是好人。
2007年8月22日
请勿开启浏览器阅读模式,否则将导致章节内容缺失及无法阅读下一章。
相邻推荐:乡野小神医 警告!黑客侵入(穿越) 重逢孟医生后,陆总每晚都想贴贴+番外 帝王的宠妃是个O(穿越) 张扬 异界也可以刷副本 情感亲密应激症 赤星战朝 顶级伪装 你说不穿裤子【短篇集】 我,胖头鱼,超凶! 沽名钓愉 全服最强散人玩家 总裁的挚爱 以茶入药(年龄差H) 永无宁日[无限](穿越) 三句话让男人操了我十八次 金风玉露(作者:白芥子) 我靠算卦横扫豪门(穿越) 大魔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