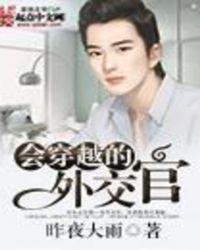京鸿小说网>补玉山居经典语录 > 第23页(第1页)
第23页(第1页)
所以他的腹稿打了几十篇,一篇都不中他的意。直到李欣起身告辞,他还在心里涂改腹稿。李欣走到楼梯口,他居然送到楼梯口。她叫他别送了,电话响了几回都不接,不好吧?然后她说没想到她和他是那样认识的,起头起得那样不愉快。
他突然明白了。她什么都知道。有关小董和他温强的一切,她全了如指掌。她怎么可能不知道呢?有多少人屁颠颠地为她这样的女人提供情报?她知道了董向前二十四岁的一条命白白葬送了。然而她连句道歉的话也没有。他理解这对于她是不堪提及的。提了或许会极度不适或伤痛。但他不能忍受她的无歉意。连他在董向前那扁平的坟前,都痛表歉意,一而再、再而三……
李欣下了两级楼梯,转过脸,说他还傻愣什么?电话快响爆了!她眼眶微微发红。这女人想干什么?真的,这是个摧毁人意志的女人。他一步跨到她身边,狠狠搂住她,吻也是狠狠的。
她满眼惊诧,但那只是一瞬。立刻就闭上了眼,这会儿把她捺倒在楼梯上,她都不推不踢。
他听见楼上有脚步飞快地下来,便松开她,转身上楼梯,回办公室去了。她自找啊,这个生来就是让男人跟她犯错误的女人。温强没回头。他进了办公室半天了,浑身还在发抖。事情过去一年之后,他什么时候想到那个吻,仍然会抖。小方在他身边也无助于事,他照样会想到那吻,那颤抖。
北京的雪渐渐少了,人却越来越多。到了八十年代末,即便下雪,也没什么赏头;当初那种恋人的雪,静谧雪白,已不复存在。大概也因为真正的恋人不复存在。亦或许因为他和小方不再是恋人,他因而失去了恋人的境界,不再看到那种境界所提供的雪景。一切是人心境的投射,这话是他在某一本通俗禅学书里读到的。几年前他到门诊所李欣的诊室里,看到她柜子里的图书收藏,除了《月亮与六便士》,还有这些杂七杂八的书。他把那些书名大致记在脑子里。虽然他无论如何也消受不了《月亮与六便士》,他却与这些通俗哲理书相见恨晚。他读了李欣读过的书,是否想解构她的内心,他不得而知。
当他终于拒绝小方出去玩雪的请求,他已感到中年的迫近。那迫近在渐渐增厚的皮下脂肪中,在不再丰厚的头发上,在他看到窗外落雪而缓慢地翻过身,接着入睡的倦怠里。小方说那么早公园说不定挺安静的,不会有那么多双脏脚片子把雪原耕翻,弄成一块灰白庄稼地。她央求他快起来。他听见自己像猪一样哼哼着,一则表示在享受没出息的舒适,再则表示抗议。
他和小方从此取消了玩雪这项活动。那时他们在等待机关分房子,好生孩子,起小灶做饭,也好有地方晾尿片子。他眼下躺着的双人床放在这间前办公室的角落,和其他区域仅一帘之隔。其他区域包括书房和客厅,以及简易厨房——只是一口大电饭锅,下面煮,上面蒸,要是炒菜,还得一个手指捺紧开关键,免得它跳起来熄火。甚至还有一个简易厕所,一个双节便盂。走廊两头的公共厕所一旦客满,他们可以用它应急。温强的中年征候也在于对生活形式的马虎:刚结婚搬进这座老办公楼时,毙了他他也不肯端着鲜艳的双节大痰盂在走廊游行,和端一锅稀粥或一盘粉蒸狮子头的人擦肩相错。结婚不久,小方迫于经济结据,去一家大宾馆做合同工,也是总机员。那时流行开公司,宾馆套房门上全是“英福特”、“海泰克”之类的洋名字。谁也不明白那些公司根据什么起了那些洋名字,但听上去相当跨国。小方两年之后从电话线上认识了几个洋名字公司的“总”,不是“王总”就是“李总”,最后终于调到公司做秘书去了。一个晚上她从头发梢打扮到脚趾尖,同时说有个朱总想雇一个办公室主任,她推荐了温强。朱总安排小方带温强去面谈。温强问这个朱总是不是也是从电话线里爬出来的。小方说那当然,不过比其他从电话线里爬出来的“总爷”们要地道一点。
直到温强停职留薪为朱总工作了三个月,他才意识到自己曾经许的诺——那个伟岸男子的诺言:“老子养你!”他差点儿给自己一个嘴巴,因为他几乎笑出来。现在小方挣钱比他挣得多,几乎是小方在养他。又一想,他对自己说:管它呢。
“管它呢”也是严重的中年症状。
他是在见到李欣后一一检数自己中年症状的。李欣重现在曾经的“老铁”兵部大院,离温强给她的那个吻,已有五年。文化科曾经属于温强的小办公室里,坐着的是一大摞大鼓、站着的是一排排立式风扇。李欣正从门上的小窗看里面站着、坐着的东西如何挤掉了温干事的席位,一个人在她身后问她是不是小李大夫,是不是找温干事。那是一手提溜了四个暖壶的曾经的勤务兵,现在一点儿兵样都没了,说他自己从一楼跟到她二楼。温干事调走喽。调到哪里?调到什么国际大公司去了。
温强听李欣向他描述这段苦寻过程时在观察她。她美还是极美的,又添出贵气来。加拿大、美国都住过了,仍然很大很亮的眼睛添了点儿不以为然。她穿了一条淡蓝的布裙子,头发养得又长又厚,笑的时候头发也是笑的一部分,散了她一脸,再挥往脑后。她留长发是为了显嫩吗?天知道这女人要把少女做到几时。
温强接到李欣的电话,便赶到这家“波士顿海鲜馆”。他不知自己会不会把这餐幽静秘密的午餐告诉小方。武官夫人用抱怨的口气炫耀她的国际生活,她如何的累,因为她成了大使每次酒会的女东道主;她多么的烦,每两年来一次国际大搬家,多少时髦的衣服都在搬家中运输不当而发霉。温强的话很少,看着她涂着粉色唇膏的嘴唇一开一合,他得一次次捺住本能。
“婚后生活怎么样?”她话题一转,突然把泛泛的谈话收了尾。
“挺好啊。”他说。他的声音有这么个意思:不就那么回事吗?
“那时候我还以为你会追我呢。”她装着厚皮厚脸,过来人似的咧嘴笑。这种笑不适合她。
“我也以为我会追你呢。”他浑身一麻。他的本能在让他眼放绿光,他可管不住它。
“那你怎么没追?”
这个女人又来了,惹出事情又全是你兜着。现在她做了人家的老婆,更是单刀直入。
“我追得上吗?”他说。
“不追你怎么知道?”
“拉倒吧。”
“其实你都开始追了。”
她似乎要拿五年前那个吻来赖住他。他一时真糊涂了:自己是爱死了她还是恨死了她。
“我追有屁用。”
“你怎么知道没用?”
“我一个农村娃子,最大的官才当到连级,一月挣那几毛钱还得寄到农村去养两对半老人。”他指的是董向前家一对老人,一对半是他自己的父母、祖母,但她显然理解成他的丈人家。“你说,我追你有用没有?”
她垂下眼皮,嘴角用一点力挑起,玩火或走钢丝的那种越刺激越玩的笑容。然后她睁开眼睛,神色凄惶了。她慢慢地摇了摇头。
他想这女人还是天真的,诚实就是她天真的一部分。她曾经在电话上对自己现在的丈夫挑衅,说她的追求者中有个姓温的。虽然有些栽赃的意思,但他不由得还是赞赏她的诚实。
“你看,你承认我即便追求,也没用。”
“什么意思?什么叫‘即便’?好像你当时没追我似的!”
“我怎么追的?”他脸上那点恶棍笑容他自己仿佛都看见了。
她瞪着他,马上又撩开披下来的长发,同时舔舔嘴唇。她的嘴唇像一朵花。花是植物的性器官。她长这样的嘴唇,人家吻她,她还跟没事人似的。那吻可不是追求。是什么呢?他现在不想向自己挑明。
请勿开启浏览器阅读模式,否则将导致章节内容缺失及无法阅读下一章。
相邻推荐:吴川是个黄女孩(出书版) 一个女人的史诗 余华短篇集 谁家有女初长成 许三观卖血记 幸福鱼面颊 无非男女(出书版) 也是亚当,也是夏娃 兄弟 穗子物语 雪地里的蜗牛奄列(都会爱情系列) 无出路咖啡馆 我微笑,是为了你微笑 十个词汇里的中国 白蛇 毕业歌(出书版) 一九八六年 在细雨中呼喊 铁梨花 我们生活在巨大的差距里